原标题:细节决定成败——HBSN杂志(IF:3.911)编辑部的故事 连载05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用汪道远社长的话说,也可谓是“成功没有捷径”。AME旗下有六十余本期刊,几乎每一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汪社长看来,“主编的勤奋、严谨、认真也代表着HBSN杂志的风格——一位主编的习惯也会直接影响到一本杂志的定位和方向。”
似乎记忆里只要汪社长提起HBSN,都会提到毛教授的勤奋——“我们常常在早上6点多收到毛教授发给编委、作者等等的邮件,可以感觉到他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打开邮箱看邮件、回邮件,7年如一日,”而且,汪社长特别强调,这与杂志是否被SCI收录并没有关系,“在杂志还没进SCI的时候就是如此,毛教授为这本杂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前前后后负责过5本杂志的科学编辑“老人儿”郑思华说自己接触过的主编也已经有好几位了。她感慨,毛一雷是一位“真的把这本杂志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培养”的主编,“各位主编都有各自对待杂志认真负责的方式,而毛主任的特点是像在陪着自己的孩子一起长大一样,从孩子的出身、培养计划、培养目标到每一步细化的细节,他都会事无巨细地安排好”。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资深编辑徐小悦。她认为,毛一雷就是HBSN杂志标准的灵魂人物,“这本杂志的编委几乎每一位都是毛主任精挑细选后钦定的,杂志的风格和定位、刊登文章的类型和数量等都由他来把关,这也是HBSN杂志的亮点之一”。
毛一雷的勤奋,从他自己描述的每日投入杂志的时间也可见一斑。“我一般早上6:20~6:30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先泡一杯心心念念的绿茶,闻一下,心旷神怡;喝一口,沁人心脾。接下来我会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对于自己究竟一天中花在HBSN上有多长时间,毛一雷思考了一下,“固定的应该是1~2个小时”,但他也强调,“其实关心HBSN的时间,并不仅仅就这么点儿”。
“一种是前面说的固定时间,还有一种,也是占据更多时间的是‘思考’的时间,走在路上、吃饭的时候、查房间隙……我常常会突然想起来杂志的某件事——最近在审稿的积极性中,日本人排第一,最积极,第二是韩国、第三是意大利,那是不是需要纳一些新鲜编委来鼓励一下?前两天在上海开会碰到的那位韩国专家是韩国候任肝胆学会主席,我跟他提过邀请加入HBSN编委的事情,那是不是2周左右的时间发一封正式邀请函?下一步还得继续挖掘有质量的审稿,我得记到本子上……所以,布局和思考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对于毛一雷而言,也许自己的十二时辰中都有过HBSN的身影,即便在梦里。
从早上6点出发去医院,到晚上23点入睡,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一心扑在工作和杂志中的毛一雷,吃饭只是匆匆完成,衣着用他的话说也是“比较不走心”——“我的裤子不分春夏秋冬,我腰以下的衣物,基本四季都一样。”看我们纷纷流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毛一雷解释,“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活动嘛,再多也就是会议会场,而基本这些地方都有空调,四季温度也不会差别很大,所以我从来不穿秋裤、毛裤,我穿的西裤、袜子四季几乎都一样,我也不用花时间去想它、管它”。“因此都受到女儿鄙视”的毛一雷坦言,自己只有衬衣和外套会分一下夏天和冬天,“我的鞋也就是两双,来回交替穿,甚至出去旅行,我也就是只有这两双鞋”。
在杂志被PubMed收录之后,毛一雷曾经去过汤森路透总部两次进行汇报。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让西方世界真正了解中国人办的杂志是什么样子的”。近些年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办的杂志、中国人投的文章,在西方世界中有一些不良影响。而在这样的背景下,HBSN、毛一雷在稿件的来源和认可度、杂志的推广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凸显出杂志团队在创办一本“体面”的杂志上的决心和耐心。
4月25日,毛一雷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是他第二次拜访汤森路透总部的时候,自己跟汤森路透编辑和出版关系部副总裁James Testa及其同事Matt Rice相谈甚欢。对方坦言,之所以能再次接见他,第一就是因为HBSN杂志的稿件质量,近年来这本杂志文章的被引用率上升主要也是依靠杂志过硬的质量,以及杂志团队不遗余力的推广和宣传;第二,这本杂志也打消了他们之前对于中国人办的杂志的疑虑和误解。毛一雷回忆,离开的时候,Matt特别将他们一行送到了门口,而这在以往是很少有的事情——毕竟他们每天要接待大量来访的人。Matt在门口对毛一雷推心置腹地说:“你是一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理解西方人行为习惯的中国人,你们这本杂志做到了真正的‘国际化’,我们非常支持你,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办出有自己风格的杂志来。”
听到这里,毛一雷心想,“有谱了!”从Matt亲自送到门口开始,他就知道有希望了,而听了Matt的话之后内心就越发确定杂志被接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果然,他的预感得到了印证——临行前,Matt最后提醒,“6月初记得给我写一封信,说明一下你和杂志的名字,还有4月25日你曾经来过我这里。”
第一封,5月初。“西方人的习惯是拜访回去后要礼貌性地回一封信,以对对方的招待表示感谢,所以我肯定是要先回一封的。我考虑了一下,从4月25日到6月初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一定不能让对方忘记了我。但这封邮件又不能离25日太近,因为如果太近这封邮件就没有意义了。我需要让他能有一段时间、最好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快忘记又还能想起我的时候提醒他一下,所以我选择了5月初发出这封感谢他之前热情招待的邮件。”
第二封,5月中下旬。“虽然他说让6月初给他一封信,但从5月初到6月初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太长了。我需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再次提醒他要记起我。于是我选择了5月中下旬,内容是关于我在近期的一个会议上遇到了他的一位校友,也提起过他等等事情。他的回复信也提示,他还一直记得我。”
第三封,6月1日。“这是之前他提醒过我的,要我说明4月25日拜访一事,以及杂志的名字等等,于是我在这个时间照做了。信的内容非常短,但我邮件subject(主题)特别用了‘Remind from Dr. Mao of HBSN……’,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土’,但实际上这很重要,包括我后来会讲的我们的邮件主题、内容等等细节,这些都是促成杂志成功的一个个重要因素。看到这个主题的人百分之百会打开这封邮件,我有这个信心。意外的是,发过去之后1分钟不到,弹出来一条自动回复消息:我因事外出,如有事请与我的秘书联系……千万不要相信西方这样的自动回复邮件,因为此刻他的邮箱里已经积压了成百甚至上千封邮件了,而你的这一封,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场景是,他离开办公室1周左右的时间,等他回来的时候,打开电子邮箱,里面已经有几百封邮件,即便我的邮件主题做了提醒,也会照样石沉大海。等他按照每天5~6封的回复速度,等轮到我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6月20日。我绝不能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四封,6月5日。“我看了一下自动回复的时间,推算了一下他应该是6月5日去办公室。我在自己的日历本上记下了这个日子。按照他6月5日早9点进办公室,考虑到他在东海岸,加上时差,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6月5日晚9:15左右打开电脑。为什么不是9:00?因为他进办公室一定不是第一时间开电脑看邮件,还要加上寒暄、喝咖啡等的时间,所以等他能坐下来打开电脑,至少要到9:15。所以,为了保证我的邮件正好在他打开邮箱时的最上面,我需要计算好这个时间。所以我在邮件中说明,我按照你之前的提醒,6月1日(如下)曾经给你发过邮件,但因你有事外出,故今日再发一封……”
5个小时后,6月6日凌晨2点多,毛一雷醒来,打开邮箱,看到里面静静躺着一封回信,大致内容是:祝贺你,HBSN杂志已被获准进入SCI,再过几周,你会得到正式的通知。
“我相信,他一定能体会到我的用心良苦。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细节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人估计并不多见。那天我记得我很开心很开心,我吃了很多很多的饭。”
毛一雷对于细节近乎“疯狂”的追求也被深深地烙印在HBSN的日常点滴中。毛一雷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让杂志符合规矩。
什么是规矩?规和矩,原意是画圆形和方型的两种工具,故常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而现在规矩多指一定的标准或法则。在杂志的日常工作中,电子邮件是最常见的联络方式,而英语是基本的交流工具。因此,基本上科学编辑们很多都要求是医学英语专业出身,工作中对她们英文听说读写的要求也较高。即便如此,毛一雷要求,每位编辑发出的英文邮件无论格式还是语法都要精益求精,不能有一丝马虎,否则之前作出的努力都会白费。尤其是在被SCI接收之后,“每个英文单词都要无愧于这个水平的杂志应有的水准和现有的分数”。
以英文邮件为例,按照杂志当时最常见的11种邮件内文格式,毛一雷指导编辑们做成了11份模版。首先,由编辑拟初稿,之后他送到曾经担任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编辑的照日格图老师那里修改第一遍,第二遍由《国际肝病》杂志原编辑部主任刘宏群教授来修改,这两位都是资深的杂志编委、编辑,平时主要的工作就是编辑部英文邮件的往来,所以在处理邮件方面经验丰富,也都有各自标准的邮件格式和规范,然后再由AME旗下一本心胸外科方面的杂志Annals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心胸外科年鉴》)主编Tristan(华人,已在澳洲行医)进行第三遍修改。最后,毛一雷根据三位的修改意见,综合整理成标准的模版,作为编辑今后发邮件时的范本。
据毛一雷介绍,目前这个邮件模版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9封。因为随着杂志办刊年龄的增长,面临的问题和情况也逐渐多样化。例如,杂志进入SCI之后,投稿量也越来越多,现在经常会出现稿件因无人审稿而被滞留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及时通知和反馈给作者目前文章的状态,以及接下来的选择,是继续等待审稿,还是转投其他杂志。这就需要不断更新和优化现有邮件模版。而且,毛一雷还会细心观察自己投给别的杂志的文章收到的回信,来作为HBSN杂志今后类似回信的格式和内容参考。
在毛一雷看来,这也体现了来自HBSN的诚意。“我们必须无愧于杂志读者、作者对我们寄予的重托和期望。细节决定成败。”
对此,所有接触过毛一雷、HBSN的科学编辑都深有同感。黎少灵曾经在2018年美国外科医师学会(ACS)年会和2018年第十三届国际肝胆胰学会世界大会上协助过HBSN杂志的宣传工作。毛一雷对细节的要求,她的形容是“太可怕了”。
“首先,毛教授把会上所有肝胆外科的讲者自己先研究一遍,之后他会分析这些人与HBSN可能产生的交集,例如这位专家适合约稿,那位专家适合邀请做编委,还有一些仅仅打个招呼即可。然后,他会在日程表上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标记、备注好之后给我们。针对不同的标记,他会给我们布置好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可以尝试约稿的我们第一句话说什么,第二句、第三句说什么;邀请做编委的我们需要拿什么去,然后说什么,下一步动作是什么;打招呼的应该说哪些话,怎么说……”黎少灵觉得,毛教授与其他专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大多数专家交代工作时重点是要求结果,但具体怎么执行不会这么详细,所以编辑需要有更多的思考,而毛教授则是把思考环节前期就帮忙做好了,并且顾及到所有细节,重点是“认真负责,执行到位”。
“很怕自己哪里没做到位,不符合要求”是徐小悦最初与毛一雷打交道时的最大担心。她说,刚开始跟毛教授一起工作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敬畏感。“毛教授有个黑色的笔记本,非常经典,上面记录了所有他认为应该在当日、当周、当月完成的工作。每次他在本上打勾时,我心里都会油然升起一股‘主编这么认真,我也要好好工作’的决心。”
一次毛教授请她还有其他编辑一起去一个很棒的餐厅就餐,但她的笔记本电脑一直没敢离手,“毛教授拿着他那个经典的黑色笔记本作记录,而我平时的工作习惯是用笔记本电脑,所以看毛教授打开本子,我也会默默打开我的电脑工作”。即便是面前摆着山珍海味,在当时的她眼中也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她认为,这是毛教授的认真负责给编辑们的一种良性传递,因为大家是一个team,只有每个人都用这种认真的态度来运营杂志,杂志才会呈现出一种统一的风格来。“这也是一种主编的人格魅力的体现”,她总结道。
最终,杂志面对的都还是读者和作者,这对于杂志早期创刊阶段尤为重要。黎少灵回忆,“精准推送”是HBSN杂志很早就坚持的,“毛教授会根据每一期杂志的文章特点,给我们筛选出适合推送的名单。原则是这些人的研究领域与这些文章比较契合和匹配,他们可能会对这篇文章更加感兴趣,因为自己也在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而对于名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杨华瑜再清楚不过了。“毛大夫会按照主题词搜索全世界在这个主题词下发表文章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专家,分别列好姓名、单位、邮箱,来做到‘精准’定位和推送。”同时,他也会通过一些新的、热的领域搜索全世界最有话语权的专家,邀请他们写稿、评论等,请这些专家更深入地参与到杂志的工作中去。
“毛教授从来不说完美这个词,但他会用实际行动去兑现自己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现在HBSN杂志的主要负责编辑郑思华讲了一个小故事:为了在国际大会上能有一个简单的杂志介绍,毛教授决定制作一个类似名片、但又要比名片更详细的宣传页,思华回忆,“不夸张地说,前前后后修改了不下几十次”。封面摆放位置、主色系选择、字体大小和行距、有的文字斜体有的粗体……“因为执行具体修改工作的是美编组同事,所以还需要把毛教授的意见准确地传达给同事,然后毛教授又是没有微信的,只能电话……”所以,过程中的挑战可想而知。思华说,有一天电话沟通完毕,毛教授突然问她:有没有觉得不耐烦?她赶紧回答:没有没有。毛教授进一步解释:这个虽然是个小宣传页,但如果有一个细节没做到位,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会白费。因为我们这个宣传页是要拿给全世界的医学专家看,如果因为这个细节没做好,很可能对方对我们这本杂志的印象就难以挽回了。
在大家看来,毛一雷之所以能做到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通过优化杂志的每一个细节,来不断优化读者和作者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而毛一雷本人强调最多的是——“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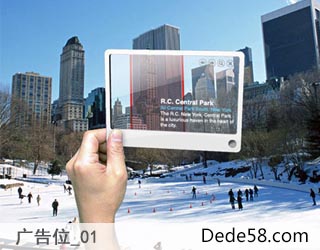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