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哈布斯堡王朝:翱翔欧洲700年的双头鹰》,作者:[英]卫克安,译者:李丹莉、韩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查理费尽周折地支持他女儿作为理论上的继承人的地位,却不注意动用军事和政治力量来保障她的皇位继承权,他的心思由此可见。查理意外身故的时候,她得到的是一支衰弱的军队和一个几近空虚的国库。财力都被用在了他新建的图书馆、教堂和其他建筑上面,也用在了新的美泉宫上面。购买艺术品、书籍和手稿,以及花在赫尔格特的《外交史》(Genealogia)工程上的钱还算是小头。1740年的时候,查理身体特别健康,心里还盘算着再婚。玛丽亚· 特蕾莎与弗朗茨· 斯蒂芬在1736年11月已经成婚,到1740年夏天的时候,皇帝已经有了3个外孙女,但还没有孙子。接着,6月时他的长外孙女夭亡,但是7月时他得知他那很会生养的女儿又怀孕了,也许怀的是一个未来的皇子。10月初,他像往年一样动身去法沃里达宫打猎,希望能在新锡德尔湖(Neusiedel Lake)湖畔猎获大批的鸭子。天气很不好,一连多天的低温,天空灰暗,不断下雪或雨夹雪,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挡皇帝去从事他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他到打猎休憩地的时候有点轻微的腹痛,但是没有理会。经过了多个极为寒冷的日子以后,疼痛加重,可他照样我行我素。
10 月10 日的晚上,他的厨师为他烹制了炖蘑菇,皇帝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因为他一整天在野外打猎,回来时很饿。到了夜里,他的病情变得极为危重,他的随从紧急把他带回维也纳,一路上查理都在呕吐,不省人事。回到床上,在御医的照料下,他看起来好多了。但是第二天他的病情再度恶化,不管怎么说,他很显然病得不轻,要不行了。他的家人聚集到他床前,但是他指示玛丽亚· 特蕾莎不能来见他,怕他憔悴的样子会让她流产。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给他的大臣们下了指示,接受了神职人员的抚慰,与所有真正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一样,准备好从容离世。早上6点,他手握十字架,在皇子、国王和皇帝专用蜡烛烛光的环绕之中逝去。他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个男性成员,享年56 岁。如果他能跟他的父亲活得一样长,也就是再活9年的话,他家族的历史和整个欧洲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了。

他的去世让一个23 岁的年轻女性成了王位继承人。虽然按照《国本诏书》的继承条款,多数欧洲国家和国王自己的政治集团都同意了玛丽亚· 特蕾莎继承王位,但是她的弱势地位很快就显现了出来。普法尔茨选侯爵称她为“玛丽亚· 特蕾莎大公夫人”,西班牙国王的逻辑更严密,称她为“托斯卡纳大公夫人”(弗朗茨· 斯蒂芬在压力之下用洛林的公爵领地换了意大利的一个领地)。其他人也说,凭自己母亲的地位,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地盘有继承权,比如巴伐利亚公爵,他的母亲是约瑟夫一世的女儿,1703 年时查理就答应过给他们一块地,而1713 年时却反悔了。还有一位斐迪南一世女儿的后代,虽然血缘较远但也是直系后代。普鲁士的斐迪南二世(尽管当时还不是“大帝”)命令自己的军队进驻了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公爵领地,理由是为了“阻止其他势力的侵占”。父亲去世后短短的3 个月内,玛丽亚· 特蕾莎就失去了她统治下的大片领土。对此,从英国到匈牙利的人们创作了大量漫画作品。漫画中她的形象是被好色的邻居们扒掉衣服(指她的领土)的女人。“被扒去衣服的匈牙利女王”(The Queen of Hungary Strippt)这一形象让人觉得把玛丽亚· 特蕾莎描绘成一个强奸受害者很有道理,无须隐晦,而法国枢机主教弗勒里(Fleury)常常被描绘成施害主角。在某一幅漫画中,他口说着“我来”,明白无误是一句“双关语”,因为他的双手正抚摸着她那近乎赤裸的年轻身体。在一幅匈牙利的漫画中,他的形象是正把她遮住下体的那只手给拉开。这些粗俗的画可没有什么骑士精神,所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女人不应当政的厌女情绪。

她的性别使她无法得到推举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她不断得到的却是污秽不堪的含沙射影),但是玛丽亚· 特蕾莎却把这种无法改变的劣势变成了她最大的财富。她出任匈牙利女王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匈牙利贵族的支持。传说她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小儿子抱在怀里,就像传说中的鲁道夫一世总是手持一个十字架当作权杖一样。她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奉承,还得到了一些军事力量。传说和事实很快就分清楚了,但留下的是传说而非事实。不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哈布斯堡君主,玛丽亚· 特蕾莎就变身为国母形象,同时还是不断生出健康迷人孩子的母亲。这位年轻的皇女从她出生的时候就(被预言)注定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为纪念她出生而打造的纪念章背后的画面是:她母亲身着罗马帝国已婚女性的服饰,怀抱着一个丰饶角,而她显然是从丰饶角里出来的新生儿,身处地上出产的各种果实之中。纪念章的题字是“希望重生于世”。后来,吉恩· 劳伦特· 克拉夫特于1744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奥地利皇室家族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uguste Maison d’Autriche)的法语版。这本书的首页插图就是年轻的亲王(弗朗茨· 斯蒂芬)拥抱着明显怀着身孕的女王(玛丽亚· 特蕾莎)坐在王座上。台基边上站立的是手持盾牌和出鞘宝剑的男女战神,守护着他们。女战神柏洛娜的食指指向怀孕的女王,代表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未来将始于危急时刻。
因为这位年轻的匈牙利女王,哈布斯堡家族的宣传重点谨慎而缓慢地发生了转变,原来到处都是逝去的祖先的形象,现在宣传的却是当朝的未来、多子女的母亲、骄傲的父亲,以及他们共同的孩子。从1749 年米登斯为玛丽亚· 特蕾莎的儿女们所作的画像中可以看到,画中全是活泼漂亮的孩子,3 个身着匈牙利服装的男孩,4 个穿着法式服装的女孩,8 岁的约瑟夫高高地坐在中间,手里拿着金羊毛项饰,而他的姐姐玛丽亚· 安娜正抚摸着公羊垂饰。王朝的象征(金羊毛)和匈牙利的服饰是突出的宣传主题。到处都能看到玛丽亚· 特蕾莎为了成为匈牙利女王而做出的努力。在她完成加冕礼之后不久,版画师戈特弗里德· 伯恩哈德· 格兹(Gottfried Bernhard G?z)为她作画,题为“忠诚的匈牙利”。

她的身边跪着一位英俊的骑兵,一只手放在心脏的位置上,一只手拿着出鞘的宝剑保护着他的女王。在玛丽亚· 特蕾莎、利奥波德二世和弗朗茨二世(一世)的许多家族画像中,子女众多这个特点非常突出。子女众多几乎被看成了对查理六世家族死亡和衰败的回应。约瑟夫二世兴高采烈地给他的弟弟利奥波德写信说,利奥波德在婚床上的不懈努力免除了他(约瑟夫)为家族添丁做贡献的义务。“优秀的‘造人者’,亲爱的弟弟,我多么感激你!你妻子又怀孕了。你这样做是在为国家服务,对我来说这也是无法推辞的义务。继续努力,我亲爱的弟弟,千万别松劲。放开胆子尽可能多地为王国生孩子吧。如果他们能像你一样,那就有多少生多少。”
到处都能看到多子多福的象征符号。丰饶角、裸体的丘比特等传统的象征符号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玛丽亚· 特蕾莎统治的奥地利,人们对纵欲行为很是不齿,但对做母亲这件事情可是非常看重。她自己就为奥地利贡献了13 个孩子,他们都长大成人,其中5 个一直到1800 年都还健在。利奥波德二世的16 个孩子当中,有14 个活到了成年,他的儿子弗朗茨成了最后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第一任奥地利皇帝(这使得他有了“弗朗茨二世和一世”这个奇怪的称呼),他尽职尽责结了4 次婚,生了13 个孩子。溺爱子女和注重家庭生活变成了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主题。研究法国人口(或人口减少)的历史学家卡罗尔· 布鲁姆(Carol Blum)生动描写了人们对人口数量减少的恐惧,他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错误想法,即人类正在灭绝,人的生产力几近枯竭……这种想法存在了100 年的时间,几乎无人不信。世界正遭到废弃,人类正在走向灭绝的未来。认为现在的人口比以前少了,进而认为大自然及地球都已经贫瘠荒芜的这种想法,与我们当代那种因人口增长过快而有的紧迫感正相反。这种认为世界,尤其是我们王国(这里她所说的是法国,也一样适用于或者说更多地适用于奥地利领土)已经变成了一片荒原的观点,也影响了反专制的论点,支持这些论点的是这样一种情感逻辑,即无能的君主没能完成保证万物繁荣的神圣职责。事实上人们可以想见,这种生命力下降的观点根本就是谬误,但对于一个风雨飘摇王国里那些满怀失望的当事人来说,这样的观点从心理上很容易接受。

反过来也一样,玛丽亚· 特蕾莎生养众多,也给哈布斯堡家族以力量和对未来的信心。她在刚生下约瑟夫的时候就说了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我线 个月的身孕”,表明了她要在这个“战场”上战胜一切对手的坚定决心。1741 年,她的顾问建议她跟法国和普鲁士这两个联合起来的哈布斯堡家族宿敌讲和,她告诉他们根本不需要。英国大使罗宾逊描述了这一场景。“群臣(一听说法国和普鲁士要结盟)都面如死灰,跌坐在椅子上,只有一个人面不改色,那就是女王。”后来他又写道,她说:“我只是一个弱小的女王,但是我有一颗国王的心。”如果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他一定会提起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面临玛丽亚· 特蕾莎的祖先腓力二世的入侵威胁时,对驻扎在蒂尔伯里的军队所说的话:“我知道我只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女人,但是我有着国王般的心胸,也是英格兰国王的心胸。” 甚至美泉宫也反映出了这种家庭观念。就像戈登· 布鲁克· 谢泼德(Gordon Brook Shepherd)所说的,“跟凡尔赛和波茨坦这两个政治上和建筑上的对手有所不同,哈布斯堡始终是一个家。尽管建筑庞大(共有1441 间屋子),廊台奢侈,议政厅豪华,但是处处有家的气氛,即便是那些至今仍闲置的宫殿也不例外。”经过玛丽亚· 特蕾莎的建筑师帕卡西的修改和缩减后,费希尔· 凡· 埃尔拉赫设计的第二稿与第一稿相比,即便还不能算是民用建筑规模,也已经远不是1688 年设想的那座庞然大物了。
玛丽亚· 特蕾莎的“慈母”形象能够确立,部分原因是她勇敢地生育了众多的子女,还因为与他父亲和祖父在公众场合的严肃拘谨相比,她看起来是那么不同,那么有人性的光辉。终于,事情出现转机,帝王的宝座回到了哈布斯堡-洛林这个新的家族,她的儿子在弗朗茨· 斯蒂芬的陪伴下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歌德对加冕礼的描述是这样的:
她的丈夫可以说就是查理大帝的替身,当他身着古怪的服饰在去往天主教大教堂的路上出现的时候,他举起双手让她看宝球和权杖,还有他手上戴的古色古香的手套。看到丈夫这种滑稽样子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观看的群众有幸能看到这对基督教世界里最著名的夫妇之间那种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和谐,他们不仅为此感到高兴,而且还受到了教育。当女王挥舞着手帕高喊“万岁”向她的丈夫致意的时候,人们热情高涨,欣喜若狂。
多年以后的一天晚上,玛丽亚· 特蕾沙身着便装冲进了帝国剧院,用激动颤抖的声音向那里的大批观众宣布:“我们的利奥波德生了一个儿子。”她说话带着浓重的维也纳口音,说起话来就跟她写字一样,非常有力,不讲究语法。弗朗茨· 斯蒂芬从来就没学会说德语,所以宫廷语言就变成了法语。但是他写的法文却非常糟糕,所以他妻子自己虽然对语言也不擅长,却要给他纠正明显的错误。以她轻松开朗的性格,玛丽亚· 特蕾莎显然在那个浪漫的时代里如鱼得水。可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从各方面来说,她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人。

(德里克·比尔斯描述道)她是一个全身心投入但高度自觉的母亲,她牢牢记得她还是一个君主和家族的掌门人。孩子长大离开家的时候,她逐一详细嘱咐他们该如何遵守宗教的仪式,如何保持身体健康,如何依据自己的身份地位安排饮食、履行职责……大斋节和其他苦行赎罪的节日必须严格依规进行,弗朗茨的葬礼庄严肃穆不得马虎。必须定期告解,参加团契。只能读经过许可可以阅读的书,穿着得体的服装。妻子要服从丈夫。有裸体形象的画作必须遮挡起来。
她给所有的孩子每周至少写一封信,给他们建议、鼓励和“糖衣炮弹”。就像她自己说的,她“总是希望孙辈的孩子越多越好”,于是,她不断给女儿们和儿媳们提供如何能增加孩子的数量,或是如何照顾好出生的孩子的建议。她希望孩子们能听她的话。所有的王子和公主从小就接受训练掌握一门实用技能。约瑟夫于1756 年被送到了宫廷印刷工约瑟夫· 特拉特纳(Joseph Trattner)身边学习“印刷术”。与宫廷结缘对特拉特纳一点坏处都没有,因为短短10 年时间他就坐拥好几百万财富。她的几个女儿成了成功的艺术家。但他们做这些都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的母亲一直控制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他们结婚以后也不放手。她告诉她最小也最任性的女儿玛丽· 安托瓦内特,即后来的法兰西王后,绝不能不穿束身衣,否则会破坏体形,她在许多孩子身边都安插眼线,以保证他们听从她的命令。也许不只是玛丽· 安托瓦内特,她的很多孩子都会有相同的感觉,即“我爱皇后,但是,我很怕她。”
这位女王兼皇后对记忆中的父亲(甚至是他的政策)充满敬畏,她在很多方面都继续着父亲的事业。马尔科德· 赫尔格特受命开始编撰一套更大部头的著作,此套吹捧哈布斯堡家族悠久历史的鸿篇巨制超过了他先前编撰的《哈布斯堡皇族外交史》。《奥地利皇室家族丰碑》(Monumenta Augustae Domus Austriacae)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哈布斯堡家族百科全书,浩浩8 大卷,结尾是家族墓地和遗骸的一览表。当时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纪念。她的宫廷图书管理员亚当· 科拉尔不仅将其著名前辈的8 卷书都再版了,而且再版书更加精美且备受赞誉。彼得· 兰贝修斯也在利奥波德一世的授意下,对宫廷图书馆进行了梳理,编撰出版了一套更“通俗”的缩略版。所有这些工程都由宫廷出资,但是它们引发了人们了解哈布斯堡家族历史的兴趣。人们在各个档案馆和图书馆里搜寻资料编撰关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大众版本书籍。马克西米利安的《白色的国王》在1775 年第一次刊印,这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商业投资,该书取自宫廷图书馆藏的手稿,由修道院长霍夫斯达特(Hoffst?tter)出版,书中插图全部出于布克迈尔之手。
她的另一个奇怪兴趣也是得自父亲,就是对她远祖遗骸的发掘。哈布斯堡家族的先人葬在巴塞尔的天主教堂和科尼希斯费尔登修道院,当时已经有400 多年的时间了。当然,科尼希斯费尔登修道院曾经是个谷仓,也许对于在森帕赫死于瑞士人之手的先烈利奥波德的遗骨来说不是最能表达敬意的地方。1739 年,查理六世曾命人将墓穴打开,对其内部进行检查。他去世以后,此事就搁置下来。30 年后,他的女儿让这件事情得到了善终。1770年9 月10 日,玛丽亚· 特蕾莎向伯尔尼市政府请求允许他们把所有的遗骨都迁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请求得到了批准,这些遗骨由送葬的队伍护送,重新安葬在哈布斯堡境内黑森林中圣布拉辛修道院的新墓地里。可这里也没能成为他们永久的安息之地。她孙子弗朗茨二世继位的时候,这个修道院也已经不在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上了。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在1807 年命人将这个修道院里所有的遗骸和记录全部迁往奥地利中心地带的拉文萨尔(Laventthal),安葬在另一个圣保罗本笃会教堂。从此那些遗骸就一直安葬于这个教堂的高祭坛的前面。这件事反映了玛丽亚· 特蕾莎的矛盾心理,在某些方面,她想摆脱过去的桎梏,而在其他方面又全盘接受。
她的长子兼继承人约瑟夫对自己的立场却确定无疑。他满怀怨恨(和怀念)地这样描述她母亲统治下的宫廷:
同一屋檐下集合了十二个上了年纪的已婚女人,三四个老女仆,二十个年轻的女孩,即被大家所熟知的宫廷女侍,七位公主,一位王后,两位王子,(还有)一位共同摄政的皇帝,但是根本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或者说至少没有比较理性或令人愉快的社交,因为他们都各怀心事。老女人之间,宫女之间,公主之间整天说长道短、争吵斗嘴,所以大家都待在自己屋里,哪怕要举办一个最简单的聚会,一想到“人们会怎么说”就让人放弃了……聪明人与这些愚蠢的女人在一起简直无聊至极,而最终他们找到了发挥知识的渠道之时,却用得特别不是地方。而倘若他们有机会遇到趣味相投之人,他们是不会去干那些蠢事的。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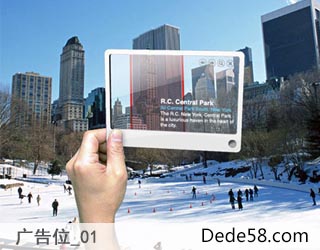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